该如何观行才能断我见?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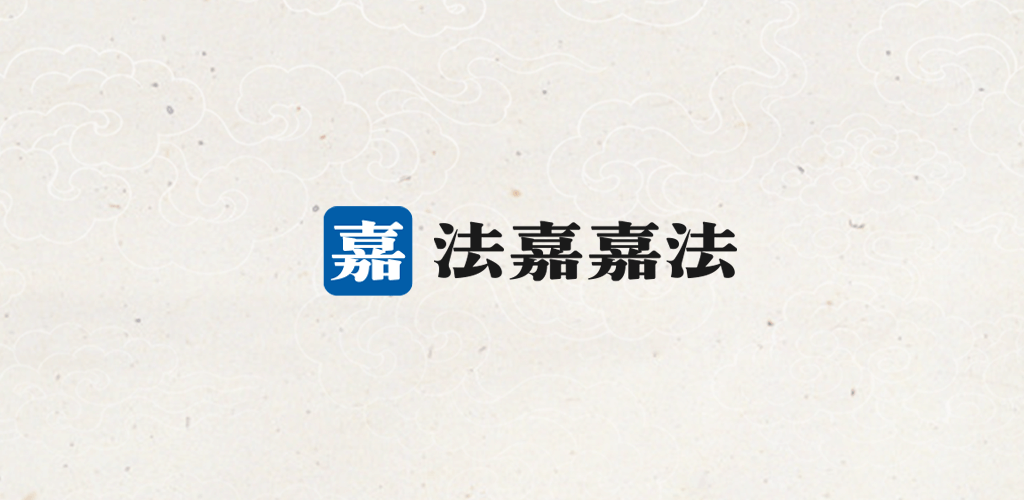
 法嘉宗智 回答
,获得 2 赞
法嘉宗智 回答
,获得 2 赞
所以一切在行,尤其目前世界各地风起云涌的崇尚谈禅,千万要注意,真正的禅宗是行到,不是嘴里讲的口头禅。光谈禅没有用,要行到,因此要特别注重达摩祖师所传的禅宗,达摩禅以二入及四行为要义。所谓二入是理入和行入,四行是报冤行、随缘行、无所求行、称法行,四种行都要做到。如果行不到,在见解上偶然有超脱的见解,在修定的心境上打起坐来偶然有一下空灵,那不是禅,那是任何人都可以做到的。
一个艺术家、文学家,乃至一个极度劳苦的人,挑个担子行百里路,偶然把担子一放,地上一坐,心情一松,此时没有杂念,很清净。要得到心境的清净很容易,可以用各种方法做到,但那不是禅。如果认为这就是道,学佛到最后什么都没学到,只学会偷懒,贪图那一点清净;而那并不是毕竟清净,真清净是功德圆满。
功德是在行上来的,不是在打坐;打坐本来在享受嘛!两腿一盘,眼睛一闭,万事不管,天地间还有什么比这个更享受?这是绝对的自私自利。但是话又说回来,打坐不需要吗?需要啊!那是先训练你自己的起心动念,或者空掉念头,或者克制念头,或者为善去恶的训练。
譬如某天有位同学答应要来这里工作,结果搞了一天就不来了,而且也不告诉我一声,这是学佛的行为吗?连这么一件小事都做不到,学个什么佛?做人连信义都没有,还学佛?什么叫信?言出有信,不来也该有个理由嘛!一天到晚婆婆妈妈说自己学佛,自欺欺人。
学佛注重在行,不在枯坐。天天在家里坐,坐一万年也坐不出个道理来啊!光打坐可以成佛?那外面的石狮子坐在那里风雨无阻地动都不动,坐了二、三十年不是得道啦?行不到没有用啊!千万注意。
《药师经的济世观》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达摩大师东来中国以后,他所传授的原始禅宗,我们暂且命名它为“达摩禅”。现在概括“达摩禅”的要义,是以“二入、四行”为主。所谓“二入”,就是“理入”与“行入”二门。所谓“四行”,就是“报冤行、随缘行、无所求行、称法行”四行。
“理入”并不离于大小乘佛经所有的教理,由于圆融通达所有“了义教”的教理,深信一切众生本自具足同一的真性,只因客尘烦恼的障碍,所以不能明显地自证自了。如果能够舍除妄想而归真返璞,凝定在内外隔绝“心如墙壁”的“壁观”境界上,由此坚定不变,更不依文解义,妄生枝节,但自与“了义”的教理冥相符契,住于寂然无为之境,由此而契悟宗旨,便是真正的“理入”法门。这也就是后来天台、华严等宗派所标榜的“闻、思、修、慧”、“教、理、行、果”、“信、解、行、证”等的滥觞。
换言之,达摩大师原始所传的禅,是不离以禅定为入门方法的禅。但禅定(包括四禅八定)也只是求证教理,而进入佛法心要的一种必经的方法而已。如“壁观”之类的禅定,最多只能算是小乘“禅观”的极果,而不能认为禅定便是禅宗的宗旨。同时如“壁观”一样在禅定的境界上,没有向上一悟而证入宗旨的,更不是达摩禅的用心了。例如二祖神光在未见达摩以前,已经在香山宴坐八年。既然能够八年宴然静坐,难道就不能片刻“安心”吗?何以他后来又有求乞“安心”法门的一段,而得到达摩大师的启发呢?这便是在禅定中,还必须有向上一悟的明证。因此,后来禅师们常有譬喻,说它如“狮子一滴乳,能迸散八斛驴乳”。
“行入”,达摩大师以“四行”而概括大小乘佛学经论的要义,不但为中国禅宗精义的所在,而且也是隋、唐以后,中国佛教与中国文化融会为一的精神之所系。可惜后来一般学禅的人,看祖师的语录、读禅宗的史书等,只喜欢看公案、参机锋、转语,而以为禅宗的宗旨,尽在此矣。殊不知错认方向,忽略禅宗祖师们真正言行。因此,失却禅宗的精神,而早已走入禅的魔境,古德们所谓“杜撰禅和,如麻似粟”,的确到处都是。
(一)所谓“报冤行”
这就是说,凡是学佛学禅的人,首先要建立一个确定的人生观。认为我这一生,来到这个世界,根本就是来偿还欠债,报答所有与我有关之人的冤缘的。因为我们赤手空拳、赤条条地来到这个世界上,本来就一无所有。长大成人,吃的穿的,所有的一切,都是众生、国家、父母、师友们给予的恩惠。我只有负人,别人并无负我之处。因此,要尽我之所有,尽我之所能,贡献给世界的人们,以报谢他们的恩惠,还清我多生累劫自有生命以来的旧债。甚至不惜牺牲自己而为世为人,济世利物。大乘佛学所说首重布施的要点,也即由此而出发。这种精神不但与孔子的“忠恕之道”,以及“躬自厚,而薄责于人”的入世之教互相吻合,而且与老子的“生而不有,为而不恃”的效法天道自然的观念,以及“以德报怨”的精神完全相同。
达摩大师自到中国以后,被人所嫉,曾经被五次施毒,他既不还报,也无怨言。最后找到了传人,所愿已达,为了满足妒嫉者仇视的愿望,才中毒而终。这便是他以身教示范的宗风。以现代语来讲,这是真正的宗教家、哲学家的精神所在。苏格拉底的从容自饮毒药;耶酥的被钉上十字架;子路的正其衣冠,引颈就戮;文天祥的从容走上断头台等事迹,也都同此道义而无二致。只是其间的出发点与目的,各有不同。
原始在印度修习小乘佛学有成就的阿罗汉们,到了最后的生死之际,便说:“我生已尽,梵行已立,所作已办,不受后有。”然后便溘然而逝,从容而终。后来禅宗六祖的弟子永嘉大师在《证道歌》中说:“了即业障本来空,未了先需偿宿债。”都是这个宗旨的引申。所以真正的禅宗,并不是只以梅花明月,洁身自好便为究竟。后世学禅的人,只重理悟而不重行持,早已大错而特错。因此达摩大师在遗言中,便早已说过:“至吾灭后二百年,衣止不传,法周沙界。明道者多,行道者少。说理者多,通理者少。”深可慨然!
(二)所谓“随缘行”
佛学要旨,标出世间一切人、事,都是因缘聚散无常的变化现象。“缘起性空,性空缘起”,此中本来无我、无人,也无一仍不变之物的存在。因此对苦乐、顺逆、荣辱等境,皆视为等同如梦如幻的变现,而了无实义可得。后世禅师们所谓的“放下”、“不执著”、“随缘销旧业,不必造新殃”,也便由这种要旨的扼要归纳而来。
这些观念,便是“淡泊明志,宁静致远”的更深一层的精义。它与《易经·系辞传》所谓:“君子所居而安者,易之序也。所乐而玩者,爻之辞也。”“居易以俟命。”以及老子的“少私寡欲”法天之道,孔子的“饭蔬食,饮水,曲肱而枕之,乐亦在其中矣。不义而富且贵,于吾如浮云”等教诫,完全吻合。由此观念,而促使佛家许多高僧大德们“入山唯恐不深”,“遁世唯恐不密”。由此观念,而培植出道、儒两家许多隐士、神仙、高士和处士们“清风亮节”的高行。但如以“攀缘”为“随缘”,则离道远,虽然暂时求静,又有何益?
(三)所谓“无所求行”
就是大乘佛法心超尘累、离群出世的精义。凡是人,处世都有所求。有了所求,就有所欲。换言之,有了所欲,必有所求。有求就有得失、荣辱之患;有了得失、荣辱之患,便有佛说“求不得苦”的苦恼悲忧了。所有孔子也说:“吾未见刚者。”或对曰:“申枨。”子曰:“枨也欲,焉得刚。”如果把孔子所指的这个意义,与佛法的精义衔接并立起来,便可得出“有求皆苦,无欲则刚”的结论了。
倘使真正诚心学佛修禅的人,则必有一基本的人生观,认为尽其所能,都是为了偿还宿世的业债,而酬谢现有世间的一切。因此,立身处世在现有的世间,只是随缘度日以销旧业,而无其他的所求了。这与老子的“道法自然”,以及“不自伐,故有功。不自矜,故长。夫唯不争,故天下莫能与之争。”乃至孔子所谓“富而可求也,虽执鞭之士,吾亦为之。如不可求,从吾所好。”都是本着同一精神,而从不同的立场说法。但是后世学禅的人,却以有所得的交易之心,要求无相、无为而无所得的道果,如此恰恰背道而驰,于是适得其反的效果,当然就难以避免了。
(四)所谓“称法行”
这是归纳性的包括大小乘佛法全部行止的要义。主要的精神,在于了解人空、法空之理,而得大智慧解脱道果以后,仍须以利世济物为行为的准则。始终建立在大乘佛法以布施为先的基础之上,并非专门注重在“楖栗横担不见人,直入千峰万峰去”,而认为它就是禅宗的正行。
以上所说的,这是达摩禅的“正行”,也便是真正学佛、学禅的“正行”。无论中唐以后的南北二宗是如何的异同,但可以肯定地说一句:凡不合于达摩大师初传禅宗的“四行”者,统为误谬,那是毫无疑义的。如果确能依此而修心行,则大小乘佛学所说的戒、定、慧学,统在其中矣。
《禅话》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真修行,必须于行、住、坐、卧四威仪中处处体会、修证“达摩四行观”:一、报冤行,二、随缘行,三、无所求行,四、称法行。
一、什么是“报冤行”?
我今天活在这世上,人家骂我、辱我、欺我、怨我,都能冤亲平等视之。一切遭遇,无论是父母、兄弟、朋友、仇敌对自己的种种,都能了解此乃过去所欠之恩怨,应该还的,所以寒山问拾得:“世人谤我、欺我、辱我、笑我、轻我、贱我、恶我、骗我如何处治乎?”拾得答:“只要忍他、让他、由他、避他、耐他、敬他、不要理他,再待几年,你且看他。”
如此作到一切冤亲平等,受了大辱都很坦然,也就同于《金刚经》所说的“是人先世罪业,应堕恶道,以今世人轻贱故,先世罪业,即为消灭。”一切都是报冤行,真修行要随时存念:“我欠这世上的债还没了,我是来还债的。”一般人能这么想到、做到吗?——难!
二、什么是“随缘行”呢?
有好的衣服就穿好的,没有就穿差一点的,甚至一无所有,从垃圾堆里捡来缝缝补补,也可以穿,一切随缘。寒山又问拾得:“还有甚诀,可以躲得?”拾得答:“我曾看过弥勒菩萨偈,你且听我念,偈曰:老拙穿衲袄,淡饭腹中饱。补破好遮寒,万事随缘了。有人骂老拙,老拙只说好。有人打老拙,老拙自睡倒。涕唾在面上,随他自干了。我也省力气,他也无烦恼。”
有人骂我,我说:“好!好!我该骂”,有人打我,我就躺下来给你打,免得被你打,还花了那么大的力气,你也少烦恼,这多好,这又多难做到,此即随缘行。
昨天有个出家人问我:“有人邀我到法国闭关好不好?”我说:“真修行,污泥中也可以闭关,我前几年不就在闹市中闭了三年关?!”当时我也曾到处找地方,后来有个桃园的同学,要把竹林老家都送给我,我到了那里,自觉好笑,就回来街上闭关,自己嘲笑自己:“昏了头!哪里不是道场,提婆达多不也是以地狱为道场吗?!”
三、什么是“无所求行”?
你们在此修行做什么?想成佛是不是?自性本空,一切都还是还债,前生欠的宿债,所有恩怨、感情都是还债,这个因果错综复杂,不过也有蛛丝马迹可寻。欠多了来生做人父亲,白手成家,辛辛苦苦经营赚了些钱,等儿女长大,自己就翘辫子了。你们的父母哪个不欠你们的,十月怀胎,辛勤养育,你却头发一剃,自己去修行,这些债主都来还你的债,如果不好好修行,你又还他们什么呢?一无报养,来生的债就欠大了,甚至也有来生变头母猪,生一大堆小猪去还债的啊!
所以,真大彻大悟者,佛也不成,凡夫也不做,大家想象得到吗?有人问我:“几时出家?”我说:“我从未入过家。”什么叫家?一个男的,一个女的,两个铺盖凑在一起,这叫做结婚成家,然后几年下来生了一堆所谓的“孝子贤孙”,长大了各奔东西。修行要清醒啊!什么叫家?——没有家!所以不用出世,也不用入世。
真修行人,一切布施,无所求,不想收回,不成佛亦不做凡夫,就是禅宗所标榜的“无心道人”。所谓:“无佛处莫留恋”——空也不住,“有佛处急走过”——有也不守。要如此反省念头,一落二边就错了。
像你们有时做劳务,搬椅子或扫地、擦窗户什么的,看看别人好好地在打坐,便想偷懒,别的同学那么舒服,我又何必这样的苦干呢?这就是“抱”怨行,不是“报”怨行,是有所求行,也没做到随缘行。大家检点平常对念头有如此反省吗?有此念头要忏悔、要舍念。
四、什么是“称法行”?
起心动念,讲话、态度、行为等等,没有不合佛法的。待人应恭敬、谦虚、慈祥,处处如此而行。但是没有慈祥,不一定不称法,怒目金刚也有深妙的道理在。
因此,如何够得上称法行?如何才不犯大乘戒?就要靠智慧抉择应用了,不是光打坐、三际托空就可以成佛,见个空性有什么用?自性本空,如果八十八结使的业力转不过来,那是永远成不了佛的。
修行人一颦一笑都要适当,不该笑时你笑,不该皱眉头时你皱眉头,都错。起心动念都要注意,有些人自以为心如止水,如果忽然骤起波涛,谁也都莫可奈何!别以为心如止水就到了,所谓:“户枢不蠹,流水不腐”,止水不动会发臭的。有人在山顶上住洞闭关,一下山来,受到凡尘外境的诱惑,那在山顶上一味清静一下就垮了,这些都是修行人的苦境。
如果自己的情绪稳定不了,想向人诉苦、向人哭泣,发泄自己心头的苦闷,这都不是修行人,应念念观察,这才叫做“守戒”。你们可参考《宋元学案》,那些理学家在行为上是律宗的精神,一言一行不敢苟且,他们讲究“惩忿窒欲”,有烦恼脾气就是“忿”,于此《百法明门论》中有载,大家必须仔细研究。因此,七八十年前的读书人,还有记“功过格”的做法,做错就画黑点,每天检查自己的过错,有欲望马上止住,如此必能征服自己,顶天立地。所以当理学家有人发现有些佛家的人修养不如他时,就起轻蔑之心了。当然他们的见地不高,但行为律仪却很有可取之处。
所以,菩萨行是一颦一笑都要清清楚楚,念念舍,提得起放得下,若能“惩忿窒欲”惯了,一上座用不着求定即在定中,此乃自性大定,盘不盘腿都无所谓,即是“不是息心除妄想,只缘无事可思量”,“清净本然,周遍法界”,此即如来大定,知道吗?
《修行人的本分——达摩四行观》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达摩祖师讲“二入(理入、行入)”,“四行(报冤行、随缘行、无所求行、称法行)”。四行里面最高的那个成就是“称法行”,就是随时随地都在法当中,随时要合法。“法”不住空也不住有,“应无所住而生其心”。打个比方,就像电插头一样,随时要插对了才行。
《现代学佛者修证对话》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严格来讲,禅宗是心宗,所以达摩祖师指定以《楞伽经》印心。《楞伽经》的宗旨,一句话:佛语心为宗。心字的问题出在这里,后来的明心见性,一切都误在这里。达摩祖师当时指出了两个方向,一个是“理入”,一个是“行入”。
理,不是普通研究道理的理,是从止观、观心的理论,进而悟道。行入包括十戒,以及菩萨的行愿,也就是在做人处事中,注意自己起心动念的一点一滴,以此证道、悟道。
禅宗的宗旨,特别注重行入。但后世研究禅宗的人,有一个很大的错误,就是将禅宗指导学人轻快幽默的教授法,当成了禅。比如这个来一喝,那个来一掌,尤其以为禅宗是见花而悟道的。殊不知那都是教育法的一种偶然机用,不是禅的真正中心。真正的中心,是达摩所提出来的行入。
《如何修证佛法》